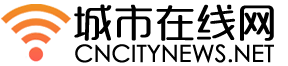一、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体现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映射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民立场,不仅是党政治立场的彰显,也是与其他政党显著区分的标志。这种立场体现在“枫桥经验”的本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中。在这两者的实践中,“人民”的概念不仅是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同样也深植于社会治理的每个环节。
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强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表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新时代“枫桥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有机融合起来,既利用国家的强制力确保法律的实施,化解矛盾,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又激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他们周围的社会治理事务中,使每个个体成为社会矛盾化解的新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这种共同体精神恰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认识人的最高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本质”不是孤立的,而是源于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反映,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时使用了“共同体”这一基础性概念,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马克思理想中的“真正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是由现实的人组成,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的社群。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不仅是个人的愿望,还是社会治理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基层社会治理转化为每个自由个体的共治活动,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价值追求的现实路径。
二、历史转折中的创新:“枫桥经验”起源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上看,“枫桥经验”起源于巩固新生政权和促进发展的历史需要。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我国经济社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基层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性社会共同体向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政治性社会共同体转变。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内外形势严峻,经济发展落后。随着美国敌对政策加剧,中苏关系走向恶化;以“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甚嚣尘上,人民内部矛盾加剧,因此“四类分子”的改造工作形势严峻。1963年,诸暨镇干部群众在探讨如何处理“四类分子”问题时,按照《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所确定的“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的政治导向,创造性地提出发动和依靠群众,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把他们团结在生产队周围的“枫桥经验”,随后,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社教运动报告公安部。毛泽东同志对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育说服“四类分子”的做法很感兴趣,当即指出: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同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蹲点研究和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2月,第13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高潮在全国形成。
三、“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共同体在多元治理中的融合与实践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共融于多元治理手段的创新性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倡导的治理内核,体现在对“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治理机制与“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维度安全策略深层次运用。通过民众力量的动员,加强法治保障与道德规范的内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村社、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三社联动”联结协同,将基层社会发展的利益多元化主体纳入一个整合性的共同体架构中。“枫桥经验”强调自治的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优先地位,以集体动员为依托保障提供社会治理的力量来源。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张基层矛盾不上交,避免矛盾层级化上升至国家法治体系层面,采用非强制性手段实现基层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呈现高度一致性。通过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群众纳入“人人有责”的治理框架之中,促使基层干部、民众以及社会组织成为治理的主力军,践行人人尽责的治理哲学,以达成人人享有的治理终极目标,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成效共享。
四、人民群众主导与自治社会的现代实践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具体化,反映群众工作的方法论。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得以形成和推广的理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智慧和动力的源泉,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拥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基础工作指南,“枫桥经验”恰恰是这一路线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展示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理论强大的内生力量。
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被定义为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属于客观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即伦理范畴。马克思在揭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正确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两者的关系提升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制度及思想意识观念是从属性的、第二性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则是决定性的、第一性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国家。根据恩格斯的论述,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非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他们强调了市民社会经济关系在决定政治和国家结构中的中心作用,批判了传统哲学对市民社会的表面理解。市民社会作为一种介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结构,是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构成的,其自主性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重要制衡。由人民群众组成的社会群体可以概称为“自治社会”,这一概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市民社会”形成理论呼应。
中国实践的具体语境中,“自治社会”蕴含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治理现实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基于自治能力构建的社会形态,拥有自行化解矛盾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社会自我调节机制是以社会群体可容忍度为界限兼由足够灵活的方式根据需要对内部个体一系列行为作出调整,以控制群体相对稳定性的自发机制。这种“自治能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内生力量,是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治理自然演进的产物。
当社会内生力量被过度抑制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一元化”的结构。反之,如果这些内生力量得到适当的释放,就会促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向社会结构多元化演变。自治社会的功能在于其弥补国家治理机能的不足,“枫桥经验”核心在于动员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构建实质性社会自治体系,通过激发民众自治活力,促进社会管理向着更加理性和自治的方向发展,从而逐步塑造出“国家一社会”二元均衡结构。这不仅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该经验能够持续传承的关键原因。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自治在基层治理中的生机活力更加凸显,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基层善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五、“枫桥经验”的生命力与现代化进程
在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出现与城乡转型并行之际,“枫桥经验”所代表的政府管理与社会协商的良性互动模式,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确保了人民群众在乡村善治中的主体地位,并以此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一诞生于浙江绚烂土地的治理智慧,其价值在于其慧根深植于民本的泥土中。“枫桥经验”不仅是基层治理创新的杰作,这一经验以其独到的治理艺术,展示了如何在乡村土壤中孕育出现代治理之花。它不仅成功化解基层的矛盾纠纷,还创造性地将党的领导、法治建设和德治文化融为一体,成就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它将党的领导与群众自治完美结合,使群众既是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更是公正的裁决者。实践证明,只有当治理脚踏实地、深入人心,才能使得政策不断接地气,得民心,从而构筑起社会稳定和谐的坚固堤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村面貌日新月异,“枫桥经验”依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与时俱进,不断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步前行。这一宝贵的治理经验,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社会治理宝库中的瑰宝,其光辉将会照亮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未来之路。